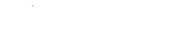【正确答案】:
《桑树坪纪事》不仅以深刻的历史内涵、时代的思想高度,成为新时期十年话剧创作的一个总结,而且也是话剧艺术探索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该剧艺术探索的成功,在于为民族自省和历史反思的总体构思找到了完善恰当的戏剧表现形式。其主要特点是:首先,《桑树坪纪事》是布菜希特叙述体戏剧特征与传统戏剧特征的结合。布菜希特强调理性,让观众保持理性思索,强调戏剧的思索品格。剧作者服从于民族自省和历史反思的思想内容,自觉地接受布莱希特的戏剧观,就是说不想单-地展现黄士高原苦难中的风情,再现愚昧.野蛮、封闭的历史,使读者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幻觉,因此采用歌队舞队来保留小说原作的叙述、议论特点,目的是要间离读者观众,使之产生“陌生化效果”;这样读者观众就可以用理智随时调节、节制感情的倾注和宣泄。例如月桂离家远嫁,歌队唱起了主题歌;村民们围猎彩芳和榆娃,歌队又哼起了无字主题歌。歌队引发人们对戏剧场景的思考,歌队的演唱体现了叙述戏剧的特点,具有感情升华和历史反思等多种作用。但是纯粹采用布莱希特的叙述体戏剧,读者观众对剧本舞台上的冷峻会受不了,感到距离太大。所以,剧作者为了尊重人们的欣赏习惯,又注意保留了传统戏剧的特点,安排设计了戏剧性的情节,人物性格的撞击、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让读者观众动“情”。由“情”推动读者观众对展现的生活现象的关心,对人物命运的关切,由“情”打开读者思索的大门,借助剧情的发展揭示生活中更深一层的东西,最终达到情理交融,激发人们对人物命运、生活本身哲理性的思索。
第二,《桑树坪纪事》运用了再现原则和表现原则,并使两者结合和交替,换言之,也就是大写实和大写意的结合和交替。剧作者在创造舞台形象时强化着自己的主观意识,并将这主观意识予以外化或物化,但往往不是在戏剧冲突发展的逻辑轨道上,也不用生活形态的自然呈现,而是运用远距离生活的形态和非生活形态的象征形象予以体现。例如,青女被“阳疯子”丈夫当众扯去裤子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场再现和写实的戏。剧作者感觉到,被扯去裤子的不是一个青女,几千年来有多少中国妇女不都是遭到封建的愚昧的野蛮的损害和凌辱?作者仿佛看到青女——这个想做母亲而不得的女人,精赤着那洁白如玉的身子,就这样躺在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土高原上。于是希望找到一种象征形象、一种象征形式来外化作者心灵的震颤,物化作者的这种历史深沉感。于是.在青女被按倒的地方,一座残缺的汉白玉的古代妇女塑像呈现在观众面前,并按剧作者的感情的要求:彩芳——另一个被封建势力所戕害的妇女——徐徐地站起来走向石像肃穆地献上条黄绫,以表达出剧作者心灵的呼唤:人们,面对着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本源——女人 大地母亲,低下头来吧!这种表现和写意的运用与处理,使剧作有了哲埋和激情的意蕴。剧中彩芳与榆娃定情的场面,老牛“豁子”被打死的场面,都糅进了表现、写意的手法,形象地表达了剧作者或赞美或愤怒的评价意识。
第三戏剧结构上的突破和创新。《桑树坪纪事》打破了传统的戏剧结构,剧作者选取了原作几个主要人物故事作为剧本结构的框架,把众多的人物或断或续穿插其间,他们将在另外的章节中循序地被聚焦,推到台前,队长李金斗或在台前或在台后贯串全剧。这里没有纵贯全剧的主要戏剧冲突,也没有回顾式的结构。
剧本保留了小说原作“人物绣像”式的特点,呈现“散文化”的格局,编织进对三个女性一个异姓人和对老牛“豁子”的围猎,真实地写人性,写人生,抒写人性,产生出“纪实美学”的亲切感。为了追求叙述体戏剧的“陌生化”效果,编剧在场面与场面,段落与段落的组接和排列次序上显示了匠心与功夫。老牛“豁子”和外姓人王志科的命运的模式大体相同,都是被“围猎”而亡的,然而桑树坪人对两个生灵的态变是不一样的,对王志科入狱是麻木的,对“打牛”则是愤怒的疯狂的。编剧把这两个命运发展的线索交叉组接,直至最后把“打牛”对比地接在“逮捕王志科”之后,这日常生活片段对比地组接,造成了布菜希特所主张的“惹人注目的-瞬”,使观众惊觉,赋予场面更多历史反思的内涵和震撼力。
《桑树坪纪事》不仅以深刻的历史内涵、时代的思想高度,成为新时期十年话剧创作的一个总结,而且也是话剧艺术探索逐渐走向成熟的标志。该剧艺术探索的成功,在于为民族自省和历史反思的总体构思找到了完善恰当的戏剧表现形式。其主要特点是:首先,《桑树坪纪事》是布菜希特叙述体戏剧特征与传统戏剧特征的结合。布菜希特强调理性,让观众保持理性思索,强调戏剧的思索品格。剧作者服从于民族自省和历史反思的思想内容,自觉地接受布莱希特的戏剧观,就是说不想单-地展现黄士高原苦难中的风情,再现愚昧.野蛮、封闭的历史,使读者观众产生身临其境的幻觉,因此采用歌队舞队来保留小说原作的叙述、议论特点,目的是要间离读者观众,使之产生“陌生化效果”;这样读者观众就可以用理智随时调节、节制感情的倾注和宣泄。例如月桂离家远嫁,歌队唱起了主题歌;村民们围猎彩芳和榆娃,歌队又哼起了无字主题歌。歌队引发人们对戏剧场景的思考,歌队的演唱体现了叙述戏剧的特点,具有感情升华和历史反思等多种作用。但是纯粹采用布莱希特的叙述体戏剧,读者观众对剧本舞台上的冷峻会受不了,感到距离太大。所以,剧作者为了尊重人们的欣赏习惯,又注意保留了传统戏剧的特点,安排设计了戏剧性的情节,人物性格的撞击、人物关系和人物命运,让读者观众动“情”。由“情”推动读者观众对展现的生活现象的关心,对人物命运的关切,由“情”打开读者思索的大门,借助剧情的发展揭示生活中更深一层的东西,最终达到情理交融,激发人们对人物命运、生活本身哲理性的思索。
第二,《桑树坪纪事》运用了再现原则和表现原则,并使两者结合和交替,换言之,也就是大写实和大写意的结合和交替。剧作者在创造舞台形象时强化着自己的主观意识,并将这主观意识予以外化或物化,但往往不是在戏剧冲突发展的逻辑轨道上,也不用生活形态的自然呈现,而是运用远距离生活的形态和非生活形态的象征形象予以体现。例如,青女被“阳疯子”丈夫当众扯去裤子是令人惊心动魄的一场再现和写实的戏。剧作者感觉到,被扯去裤子的不是一个青女,几千年来有多少中国妇女不都是遭到封建的愚昧的野蛮的损害和凌辱?作者仿佛看到青女——这个想做母亲而不得的女人,精赤着那洁白如玉的身子,就这样躺在中华文明的发祥地黄土高原上。于是希望找到一种象征形象、一种象征形式来外化作者心灵的震颤,物化作者的这种历史深沉感。于是.在青女被按倒的地方,一座残缺的汉白玉的古代妇女塑像呈现在观众面前,并按剧作者的感情的要求:彩芳——另一个被封建势力所戕害的妇女——徐徐地站起来走向石像肃穆地献上条黄绫,以表达出剧作者心灵的呼唤:人们,面对着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本源——女人 大地母亲,低下头来吧!这种表现和写意的运用与处理,使剧作有了哲埋和激情的意蕴。剧中彩芳与榆娃定情的场面,老牛“豁子”被打死的场面,都糅进了表现、写意的手法,形象地表达了剧作者或赞美或愤怒的评价意识。
第三戏剧结构上的突破和创新。《桑树坪纪事》打破了传统的戏剧结构,剧作者选取了原作几个主要人物故事作为剧本结构的框架,把众多的人物或断或续穿插其间,他们将在另外的章节中循序地被聚焦,推到台前,队长李金斗或在台前或在台后贯串全剧。这里没有纵贯全剧的主要戏剧冲突,也没有回顾式的结构。
剧本保留了小说原作“人物绣像”式的特点,呈现“散文化”的格局,编织进对三个女性一个异姓人和对老牛“豁子”的围猎,真实地写人性,写人生,抒写人性,产生出“纪实美学”的亲切感。为了追求叙述体戏剧的“陌生化”效果,编剧在场面与场面,段落与段落的组接和排列次序上显示了匠心与功夫。老牛“豁子”和外姓人王志科的命运的模式大体相同,都是被“围猎”而亡的,然而桑树坪人对两个生灵的态变是不一样的,对王志科入狱是麻木的,对“打牛”则是愤怒的疯狂的。编剧把这两个命运发展的线索交叉组接,直至最后把“打牛”对比地接在“逮捕王志科”之后,这日常生活片段对比地组接,造成了布菜希特所主张的“惹人注目的-瞬”,使观众惊觉,赋予场面更多历史反思的内涵和震撼力。